《月亮與六便》士這本書我想在我們國熱銷的原因應該是與夢想有關吧,畢竟總要給自己的詩和遠方找一個說辭,這本書無疑就是最好的理由,也許是自己天生就是這德性,在很多人舉手稱贊的時候,我總會問自己這是真的嗎?我之前寫過幾篇是關于主人公的夢想與我們的夢想,最大的區別在于他不看重別人的認可,而我們的夢想卻是把別人的認可當成一種標準。

在書中主人公的夢想與我們的夢想相比,我認為對后者的夢想理解為欲望更合適一些,這是《月亮與六便士》給我的其中一個啟示,它重新定義了我對夢想的概念,然而重新定義夢想的概念之后,我的思索還是沒有為此而停歇,這種思考來自于我們對于書中主人公的指責,難道你不愛你的孩子嗎?主人公回答:我對他們沒有特殊的感情。難道你不需要愛情嗎?主人公回答:愛情只會干擾我畫畫。
書中這個問主人公這兩個問題的那個“我”幾乎代表了我們所有人,這不是普通的質問,而是一種站在此岸世界的指責和訓斥,任何脫離欲望的夢想都會受到這般的質疑,甚至是嘲笑,我們處在一個及其復雜而且粘度極高的關系世界里,你自己根本沒有一個純粹的自己,書中主人公對夢想的追逐,是在剝離一件件的關系枷鎖外衣之后獲得的,而這種剝離我們看到了一個真正自我的殘酷現實。

有人蔑視這種自私,沒有責任心,這種掙脫社會關系的一種無情,但當他窮困潦倒的時候,當他身無分文的時候,他仍然沒有想到重新回到那個可以帶來生存和面包的社會關系中,這已經不是自私,沒有責任心,眼里沒有別人,而是他連自己都沒有的一個人,一個連自己都沒有的一個人我們怎么能讓他有別人。
我覺得沒必要對他做所謂此岸世界的道德評判,畢竟我們沒有多少人對我們所有人進行過所謂的終極評判,就如《教父》里那句經典臺詞一樣,多少的巨大財富之后都是罪惡的,當今的我們周圍,不要說巨大財富,就是一個路邊大排檔,一個小的食品加工廠,一個大桶水站,還是那些活蹦亂跳的海鮮市場,我們多少賺取金錢欲望的背后是善良的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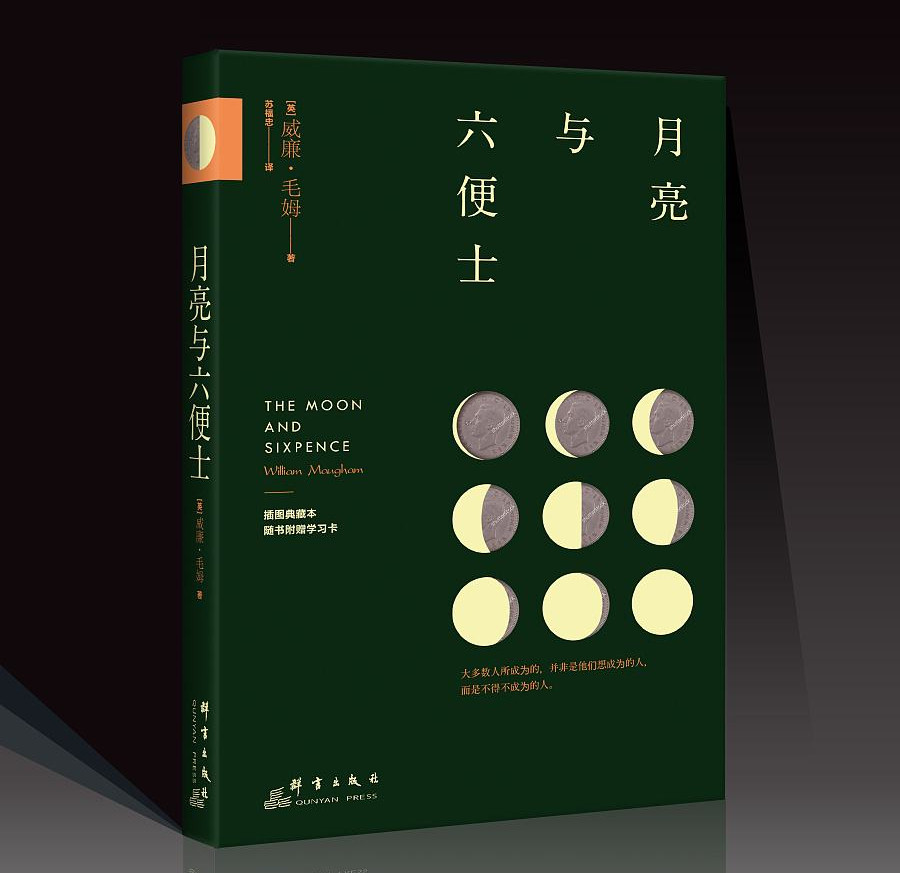
同時我也覺得沒必要對主人公的夢想過于推崇,因為真正的忠于自己的夢想的人,又有多少?我不相信一個沒有脫離“社會關系”的人值得擁有純粹的夢想,罪惡下的欲望就是對這種社會關系的最好詮釋,主人公只要還在這種關系中,必然要遵從這種游戲規則,和他的妻子一樣的“俗氣”,從一開始的否定,到最后連前夫的印刷品也掛在墻上瞻仰的時候,就注定了這是一種嘲笑,也是主人公的嘲笑。
這樣的書,能夠帶給我們對自我的思考和懺悔,我想就已經足夠,為此去定義去進行所謂理性的判斷,總歸是帶有局限性的,因為要明白最后他將畢生的作品付之一炬的行為,是需要站在彼岸的世界才能理解的吧。